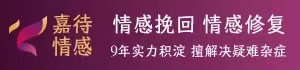斯科塞斯本人这样形容《花月杀手》:「我希望它像一支曲子,有一个事先确定的主题,但随着发展,它变得丰富和强烈,然后让人陷入漩涡。」
事实上,这电影的观感类似于一部大型交响乐的演奏现场,交织着若干主题和声部,乐队的表现谈不上完美,但重要的是音乐流动的方向。

《花月杀手》
斯科塞斯建构了亲密和暴力、悬念和罪恶、控诉和忏悔平行的复调式表达,他接受《视与听》杂志采访时说:「这个故事是关于厄内斯特和莫莉彼此相爱,核心是他爱她。」
这话不完全对。
厄内斯特对莫莉的爱渗透着毒药,很多时候是盲目又空洞的。
《花月杀手》的核心确实是「爱」,确切说,那是斯科塞斯对欧塞奇族人和欧塞奇文化的爱,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对方,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刻,他维持着谨慎的距离,遥远地打量着他们。
《花月杀手》原作是《纽约客》专栏作家大卫·格雷恩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,开篇有这样一段话描述1921年的欧塞奇原住民聚居地:
欧塞奇人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族群,纽约出版的《展望》周刊惊呼「这些印第安人日进斗金,让银行家十分眼红。」
记者用耸人听闻的故事吸引读者的眼球,「欧塞奇大亨」与「红皮肤百万富翁」,「红砖翠瓦的豪宅」与「璀璨夺目的水晶吊灯」,「钻石戒指」「裘皮大衣」「专用司机」,不一而足。
有作家大惊小怪地发现,欧塞奇女孩们在最好的私立寄宿学校就读,身上穿着产自法国的昂贵华服,小姑娘们宛如一群漂亮的巴黎少女,误入北美原住民聚居的乡下地方。
当一部分历史被长久地掩埋在不曾公开的档案中时,围绕着「北美原住民」或「美国印第安人」的刻板叙事却早已深入人心。以至于斯科塞斯第一次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灰马镇上,他意识到大部分的当地人对他心存警惕:「他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故事拍成充斥着暴力、酗酒、疯癫的陈词滥调?」富饶的小镇,飞驰的豪车,红皮肤的大亨和贵妇,酒精和暴力催化出的谵妄氛围,以及,一整个因为过分天真而惨遭残害的族群——斯科塞斯在拍摄中没有回避这类「标签化」的内容,但《花月杀手》值得注意的是摄影机的「看」与欧塞奇人之间的距离。女主角莫莉很重要,理查德·布罗迪在《纽约客》的长评里断言:「莫莉是《花月杀手》里真正的中心人物,她是影片情节的支点,她赋予了这个故事向内探索的深度。」扮演莫莉的莉莉·格莱斯顿值得提前锁定明年的奥斯卡影后。而这并不是一部让莫莉开口、「听她说」的电影,《花月杀手》的叙述视角来自白人男主角厄内斯特。格雷恩的原作起初循着白人FBI调查员汤姆·怀特的视角、继而是作者本人梳理大量未公开的资料文献,从历史的残骸碎片中拼凑出悚然的、白人有谋略地屠杀欧塞奇人的往事——流淌着石油的草原如何成为浸透印第安人血液的坟场。按照斯科塞斯最初的构想,迪卡普里奥要扮演的是汤姆·怀特,但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人物是毫无悬念的好人,以至于缺乏戏剧性的张力。之后,迪卡普里奥和斯科塞斯的吸引力都转移到原本着墨不多的「共犯」厄内斯特。从厄内斯特的视角展开叙事,这使得电影的调性完全的不同于原作。厄内斯特到灰马镇投奔舅舅黑尔,他是个过去模糊、没有来处的人,也是一无所有的人,渴望在「他人的土地」上掘金致富。厄内斯特既是将要和一个印第安女人陷入扭曲的亲密关系的「这个男人」,他也是广义层面的「美国人」的缩影。厄内斯特起初是无辜的,他不坏,也没什么能力,很快屈服于舅舅的意志,为他所蛊惑,浑浑噩噩地进入一个分工细致、组织庞大的犯罪网络里。斯科塞斯舍弃汤姆·怀特这个「清白」的叙述者,转而从厄内斯特这个「谋杀共犯」的视角接近欧塞奇族群,在某种程度上,这不仅是作品内部的悔罪意识,导演更进一步地试图把观众,至少美国观众,锚定在「有罪历史的共犯」位置上,一个也不放过。观众跟随厄内斯特的「看」,在持续变焦的过程中。舅舅和白人的世界是身边的、迫近的,在粗鄙的石油小镇里。一旦厄内斯特的视线投向欧塞奇人,那是隔着距离的另一个平行世界。厄内斯特最初被莫莉吸引、以司机的身份送她去一场欧塞奇人的聚会时,汽车驶出镇子,画面是一段短暂的空镜,春日繁花遍地,恰如一位欧塞奇族作家写下的:「广袤草原上,繁花点点,矢车菊间夹杂着三色堇,璀璨花瓣绚若星河,像极了众神遗落的五色缤纷。厄内斯特驾车离开的镇子是石油经济带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,草原花海的那边,他看到另一个与自然风土融合在一起的世界,后一个是他不曾进入甚至靠近、但参与摧毁掉的世界。厄内斯特和莫莉第一次约会时,突降暴雨,莫莉让他坐下,安静地聆听雷雨的声音。在这个场景里,斯科塞斯用一个直观的、两人同框的画面,明示了厄内斯特根本不能理解莫莉的精神世界和她归属的文化,她是他咫尺天涯的异度空间。斯科塞斯用他熟练的技艺控制着「观看」的距离游弋在「遥远」和「迫近」之间。所有欧塞奇人流淌着生命力的场面,无论生的庆典还是死的祭仪,是被隔着距离观察的。而他们成为眼前之物,那只有一种情况,就是成了白人砧板上的鱼肉。厄内斯特是罪人和爱人的复合体。他顺从地执行舅舅的阴谋,娶莫莉,逐个杀掉她的姐妹,谋取这些女人的财富。但他对莫莉是有爱的,他追求她的初衷是出于爱而不是要杀她。或者说,他对莫莉的爱并不足以让他拒绝并反抗舅舅的邪恶计划,他爱莫莉,但在白人按部就班残杀印第安人的气氛里,他的智商和能力都不足以让他不做共犯。事关杀妻的深闺疑云,这对斯科塞斯和迪卡普里奥而言都是超纲题。电影要到后半程暴力显山露水,才是斯科塞斯的主场。至于迪卡普里奥,他的局限歪打正着地制造了厄内斯特恰如其分的肤浅。自始至终,厄内斯特是没有心理深度的人,他是空洞的,像泥人一样受着舅舅的塑造,舅舅是美国梦残忍邪恶那一面的化身。电影开始的时候,厄内斯特只是一个土气的年轻人,到了尾声,他的脸接近黑尔的翻版,尤其是他们嘴角下撇的弧度,简直一模一样。以厄内斯特的肤浅,从他的视角,观众没有机会打开莫莉的精神世界。电影没有进入白人男人的心理,因为没必要。电影也没有进入印第安人的、女人的心理,因为做不到。如同福克纳《押沙龙!押沙龙!》里这段话:「我们从老箱底、盒子与抽屉里翻出几封没有称呼语或签名的信,信里曾经在世上活过、呼吸过的男人女人,现在仅仅是几个缩写字母或外号,是今天已不可理解的感情的浓缩物。」《花月杀手》制造的意向是隔着玻璃的看见,欧塞奇文化和历史的真相都不可能真实抵达了,观众和厄内斯特能看到的只是玻璃上的镜像,伸出手触摸到的也只能是玻璃。理查德·布罗迪借用斯科塞斯的旧作《沉默》来形容《花月杀手》:「莫莉、欧塞奇人和欧塞奇族在影像中夺回了主体性,但他们的主体感表现为震耳欲聋的沉默。」因为这自始至终还是白人的叙事。厄内斯特初到灰马镇,舅舅给了他一本科普欧塞奇族的常识读物,他在灯下翻开书页,舅舅的旁白念出书里的内容——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是由白人书写、白人构建、白人传播的。电影结束于一段现实进入虚构的卡巴莱式表演,斯科塞斯亲自扮演了说书人,长话短说地概括「灰马镇乃至整个美国的土地上浸透印第安人的血。」《花月杀手》拍摄完成后,斯科塞斯说了一句:「我在《花月杀手》的世界里生活了很久。」他回忆,这部电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刚拍完《穷街陋巷》,因为在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保留地的经历,他想要把1890年美军屠杀印第安人的伤膝河惨案拍成电影,当他真正能够凝视着印第安人的故事时,近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就这一点而言,《花月杀手》的核心是无可置疑的「爱」,一个创作者首先出于愧疚,继而爱上了一种他并未真正了解的文化,他以「共犯」的自省,表达迟到太久的忏悔。只是这所有的讲述,仍无法摆脱白人的立场,白人的叙事,他其实不可能为他悔罪的对象代言。斯科塞斯以他自己的身份面对镜头铿锵陈词,这个间离的场面并不让人联想布莱希特,倒更接近于变相地演绎了斯特林堡《一出梦的戏剧》:男人带着鲜花来,呼唤他看不见的女人的名字,女人是不可见的,观众只能听到男人的回声,听到回声的回声,然后男人消失了。戏结束在这里。合作邮箱:irisfilm@qq.com
微信:hongmomgs

关注公众号:拾黑(shiheibook)了解更多
友情链接:
关注数据与安全,洞悉企业级服务市场:https://www.ijiandao.com/
安全、绿色软件下载就上极速下载站:https://www.yaorank.com/

















 虹膜
虹膜
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
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